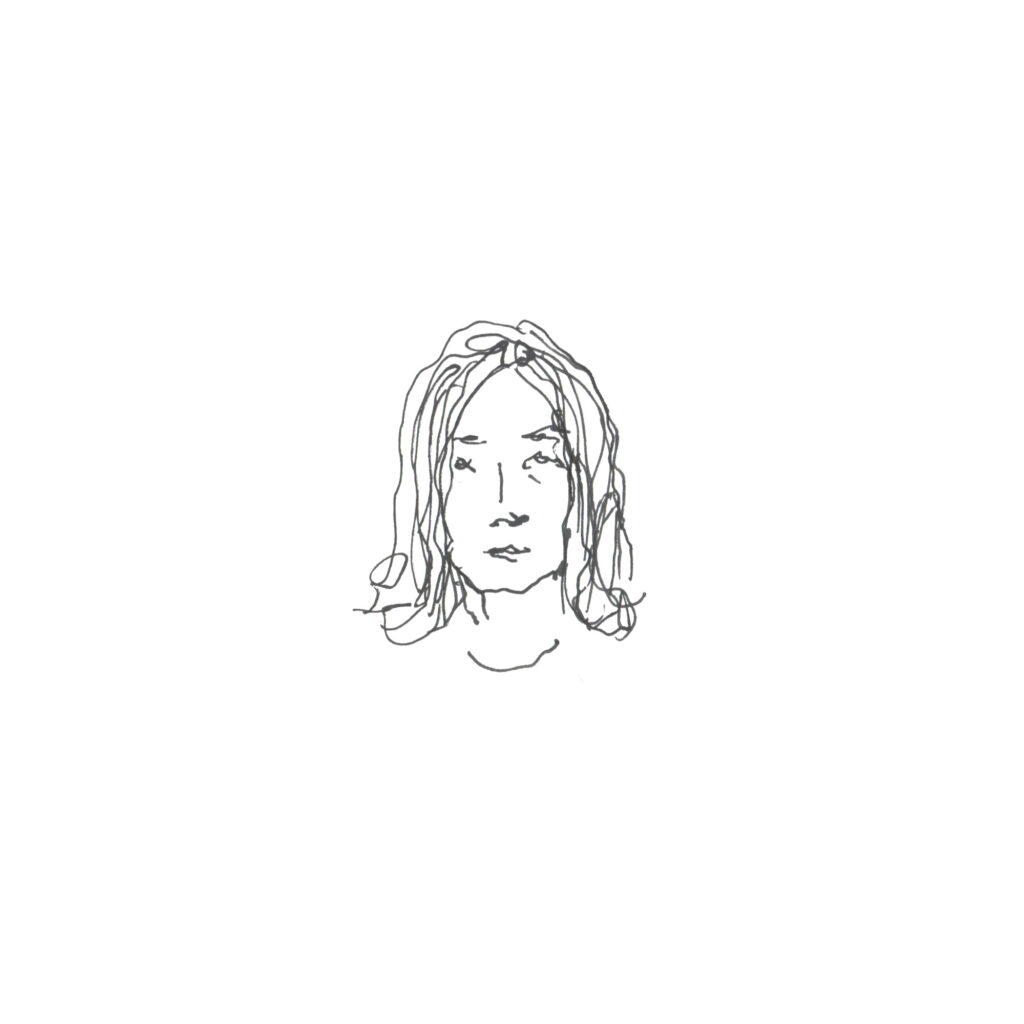——讀范俊奇《鏤空與浮雕》
為明星或名人畫像,下筆稍稍失了準,任誰都可以輕易看出來哪裡不對,那是因為我們都太熟悉那張臉了。一如人物難寫,不論精雕或白描,若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落筆分寸,如何脫開既定的刻板印象,而又不嘲不損;如何看見光亦看見影,才讓文字中活現的那人有了立體感。
范俊奇的這本《鏤空與浮雕》,就是一本閃亮的名人冊。從張國榮、梁朝偉、梅艷芳,而至安迪沃荷、海明威、草間彌生……,那目錄排開的三十個名字,無一不是閃閃耀人的明星巨匠。全書分了四輯,所寫的人物各自代表了演藝、時尚、文學和藝術領域。然而這本書好看的地方就在於,作者明白這些人都站在時代的舞台上太久了,他們在聚光燈照射底下的臉孔總是太過平面、太過晃亮,而范俊奇卻以一種近鏡頭的追攝,而讓我們看見後台人生種種,那月球背面的細節。
《鏤空與浮雕》是范俊奇的第一本書,但一讀即知是文字的老手了。范俊奇是資深的雜誌人,前後擔任過馬來西亞四本時尚雜誌的主編。他擁有著一種老派雜誌人應俱的對文化和藝術的關注、雜食和熱愛。他愛時尚一如愛詩。也因為職務之便,他經常有機會近身訪問明星,或者到世界各地的時裝秀場、展覽館。然而他筆下的人物並不是雜誌跨頁照片附屬的文字,也不是採訪明星的制式Q&A,因為他知道明星對此總是敷衍了事,所以他寫的更多是連明星也不自覺被記錄下來的一些吉光片羽。比如他寫張曼玉,「在臨上臺之前,飛快地把手指伸進嘴裡剔了一下上排的牙齒,想必是擔心完美的巨星形象在苛刻的鎂光燈面前有所閃失吧,可百密一疏,一個不小心把最不應該在公眾場合張揚的小動作給我看了去——」。
張曼玉在范俊奇的筆下,突然變得離我們很近,近得可以看見她眼尾、嘴角,脂粉掩蓋不去的細紋。他以往日浮華的風光,對比如今現實和世人對一位女明星的苛刻。這樣的光與影的描寫,一如書名所喻示的,每個人總會有另外一面,有光就有影,如撫摸浮雕,就可以感受那時間和人生的起伏。
這些人物皆變成了文字的浮雕,所以我們終於看見了原本不被記載的各種細節。如梁朝偉的眼睫毛,「像一對蝴蝶的翅膀,一忽兒深情款款地一張一合,一忽兒深情款款地覆蓋下來」。或者林青霞靈氣所在的下巴,「真像一間屋子的玄關」;以及梅艷芳露出外套的手,「那麼白皙,那麼纖瘦,那麼嫩滑」……。我們也看見了在生命最後階段深陷憂鬱的張國榮,在半夜打電話給林嘉欣,除了嘆息就僅留下了長長的空白,而無人知曉那是最含蓄也最微弱的求救訊號。
當網路的時尚達人一再對頒獎典禮紅毯上的明星衣著品頭論足,當我們對八卦新聞總是欲拒還迎,范俊奇卻看見了更多細微、內在的什麼。這也許就是這本書最可貴的部分。寫人物、寫影視時尚的專欄作家其實也不少,中國的毛尖、香港的邁克,也都是把專欄結集成書的作家。但范俊奇寫下的文字,不損人、不嘲諷,皆是對世間溫柔的凝視。他總是看見浮華而感嘆背後的頹敗,看見不朽而明白傳奇的蒼涼。
在眾聲喧嘩、無不故作姿態的現實中,不嘲諷,竟也變成一件難得的事。一如我們見過這個世間最好的電影,最美麗撼人的畫作、舞蹈或建築,而不忍對這些同時背負著天賦和傷痛的天之驕子們,再有更多的苛求。
也因此,我們原諒了范俊奇有時真的不小心走得太近,而彷彿幽靈那樣,穿過時間和身體,看見了原本被遺忘或忽視的故事和際遇。他緊緊走在人物的身旁,甚或一再走進內心的想像,更近似一種小說全知的寫法。他想像自己站在小巷子裡,而歌手朴樹站在遠遠的那端抽菸,可以呼吸到從那遠處飄過來的香菸味。他走進了芙烈達.卡蘿發生車禍的現場,描述公車傾倒、血淋淋的細節。那枝穿過肉體的鋼條如此令人觸目心驚。
這都是鑿刻出來的,月球隕石坑那樣分明的影子。每個人都知道大鬍子海明威粗獷而暴躁,但他卻寫小說家年輕時無倫的俊美。或者如此浮誇如安迪沃荷,他卻寫出藝術家在一個人的夜晚開著四台電視機的寂寞和壓抑。也只有他看見梵谷一生潦倒背後的愛和寬容,即使多窮,仍不忍陌生的女人流落街頭,而決定把自己僅剩的食物分出一半。
除了細雕的臉孔,或者我們也在這本書裡讀見了時代的變幻。范俊奇嗟嘆:「後來香港就再也沒有傳奇了」。一個電影王朝的衰敗,一個時尚風潮的遠去,文字此刻變成縷空和雕刻時光的工具,或許還可以留下一些值得我們凝視的,比如說,愛。
我們跟隨著范俊奇的文字,變換著時代的小場景,瞥見人與人之間的幽微的情感流轉。魯迅和許廣平、羅丹和卡蜜兒、顧城與妻子謝燁、基努李維和已故摯友River Phoenix;或者在此生留下八百多封信,而一個字都不提愛情的梵谷,和高更之間的愛恨糾葛。嗯,甚或梁朝偉和張國榮,曾經在銀幕上赤裸纏綿而在現實中亦如此放不下彼此——「難道那不是愛嗎?」
那不是愛嗎?這是范俊奇在這本書裡一再的提問。也許在閱歷了那麼多的人物軼事、書信和他們留下的作品,他終於找到了那不被記載於歷史的真實,或者秘密,那都是娛樂新聞和傳記一再故意忽視的,人與人之間的愛。
他說:「其實沒有誰比梵谷更懂得什麼是愛情——有些愛情像星星,必須等,等它黯淡下來會更美麗。」
愛或許是這本書鏤空出來的,不欲張揚的星光。一如安藤忠雄在大阪茨木市建造的「光之教堂」,那祭壇之後整個牆面鑿出來的空心十字架,任自然光穿過鏤空的隙縫而照進整座教堂之中。而我們也藉著這道光,才得以看見了浮世的閃亮和黯然。
而范俊奇如此附靈在人物身上那樣的書寫,走進細節而至內心。一直讀到書本的最後,我們終於明白,范俊奇真正迷戀的,「是人的繁華與荒涼,是世間的繽紛與寂寥,並且十分相信在文字中喬裝成另外一個人,扮演另外一個自己完全生分的角色,應該會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
一如作者自道:「在風流人物『鏤空』的流離歲月裡,『浮雕』出人世的眉眼與鋼索。」藝術家和詩人為這個世界留下了時間的贈禮。一幅畫作、一樽雕刻,或者一幕電影。而不管多少年過去,我們猶著迷在光影交錯的那些細節之中,久久不願離開。
(原載:台灣《文訊》雜誌.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