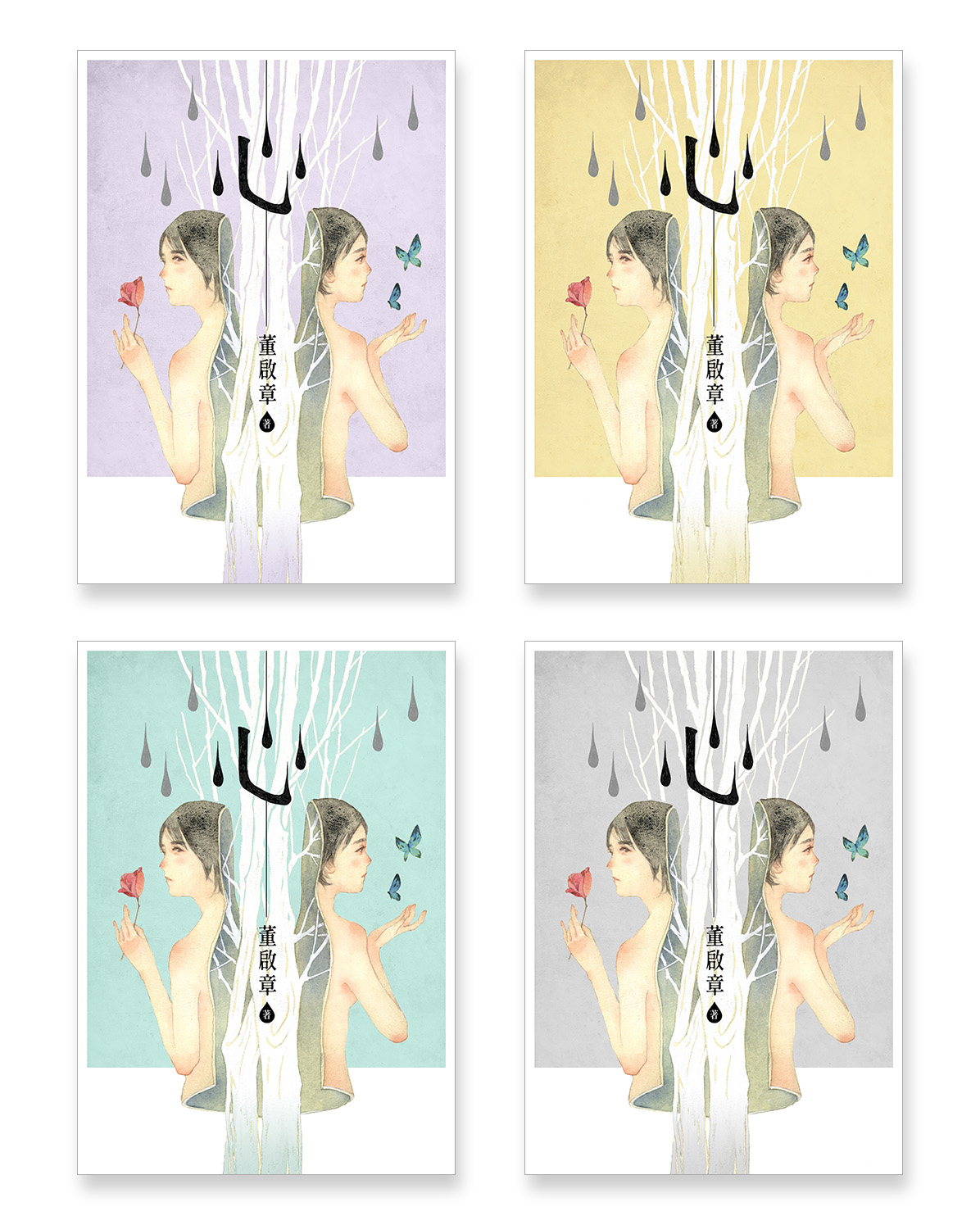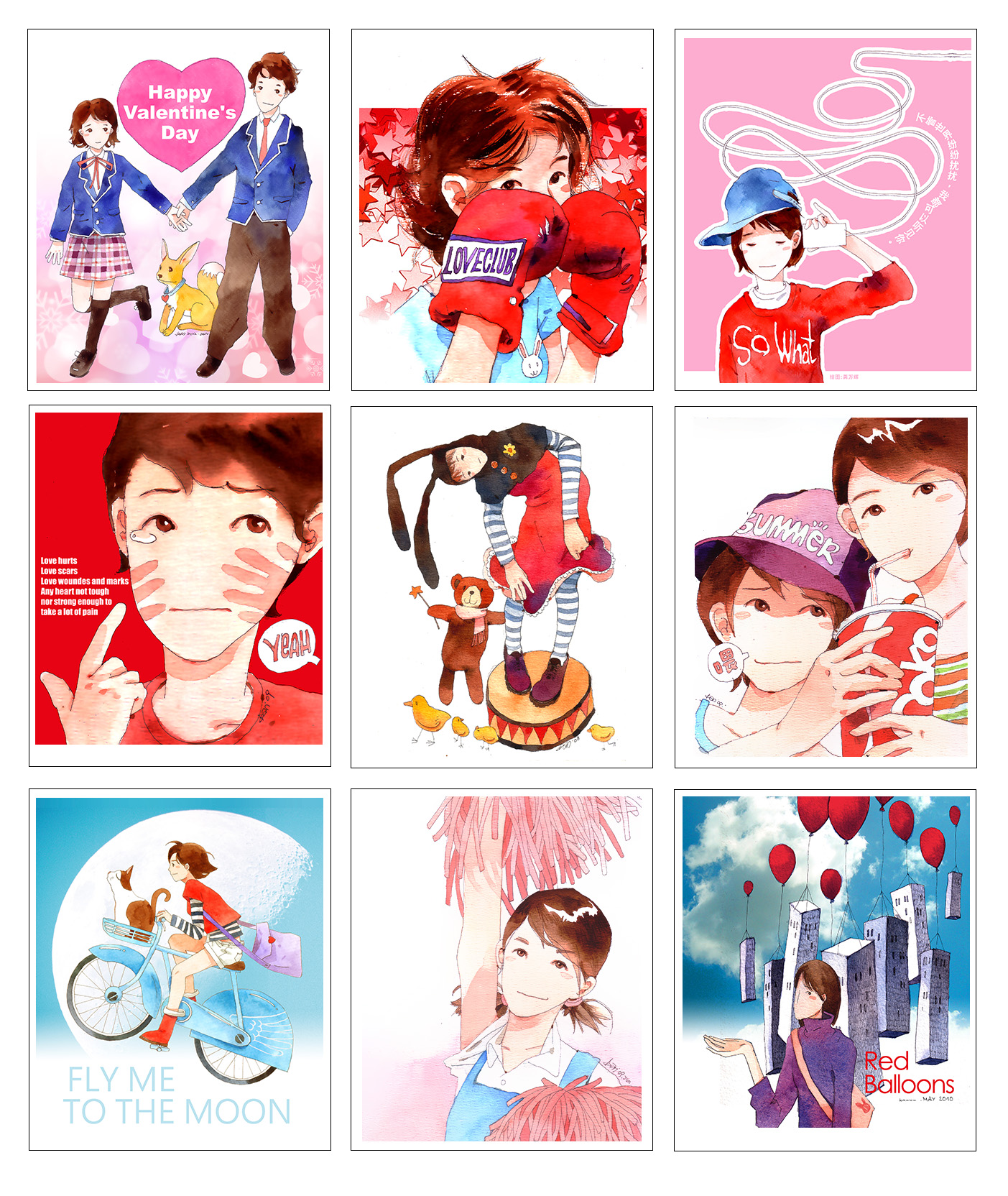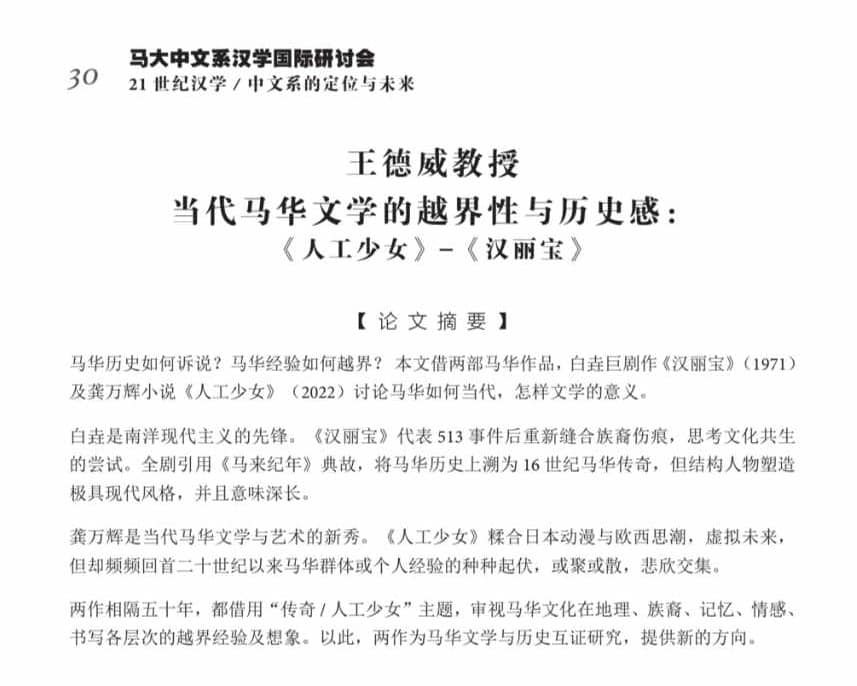——記敦煌石窟之旅
因為春天驟來的第一場雷暴雨,困在西安機場而不知何時回家。看去遠方遼闊的停機坪,一道一道閃電直擊而下,撕裂了灰濛濛的天空。心靜不下來,而機場不斷廣播的人聲一片模糊,完全聽不清楚在說什麼。原定的班機是鐵定延誤了,而沒有人知道出發和抵達的時間。我們一早趕到機場,如今卻未知接下來幾小時會何去何從。無法預見的,即使只是這麼靠近的未來。
我們能看見多遙遠的未來?如何預想,比所見更遠,比此生更遠的時間?這是我在幽暗的敦煌石窟中,突然想起的事。人類因為能想像未來,而有了文明。我們前兩天還擠身在乾燥卻冷颼颼的石窟之中。因為洞窟內不開燈,導覽人的手電筒亮起的一框,就是所能注目的一框。那些壁畫經過千年,色彩流失,卻仍可辨面目、表情。光掠過而停駐之處——那是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似乎正指引著我們終將何去何從。
當初的創造之人,是否也曾想過,手底下一筆一劃的線條,那些彩石研磨的顏料,會渡過歲月的一劫一劫,而留存到今天。眼前古老斑駁的壁畫、泥雕和建築,或許都是對人生往後的寄托和想像;又或者自知渺小,面對自然災害的畏懼,寄予佛陀以一推之巨手,而止住地動的災難。
我的佛緣尚淺,也沒有歷史的視野,只是喜歡看那些雕塑和畫像的表情和姿態。菩薩垂眉,而金剛瞠目。阿難帶笑,而伽葉肅穆。和述諸於文字一樣,浮誇易寫,而平靜的臉最難描繪。不同朝代的佛像,也擁有不同的造型、身姿、飾物和表情。有時微光掠過,原本靜止的表情似乎就有了幽微的變化。壁上也畫了當初建廟捐款的人們,而我不免眷戀世俗,往往多看一眼那些世俗人的畫像,一窺當時的服飾、妝容。
和日本、泰國的寺廟不同,敦煌、張掖的這些古老佛寺只留存廟身、佛像,而早無一僧人。那些千年佛像也不再領受禮拜(雖然仍有遊客往祂們身上撒錢幣),而悉心保留下來的這些,似乎更大的意義在於一種文明的、時光的考據。
而我身處於一千年後,身處於北魏人、西夏人、宋人,而至清人……,他們的未來。
倘若時間足夠遠,倘若有人看得見,壁畫上的鉛白氧化成黑,一個帝國煙消雲散、徒留史記。沙漠綠洲的泉水從滿月慢慢乾涸,變成月牙。當無人辨讀失傳的文字,而時間沒有停止前行。當一切皆空無常,而眼前被留下來的這些,關於未來的種種具象的描繪,似乎才讓人對殘酷的現實稍稍地感到一些釋懷吧。
於是一夜無眠,我們才終於搭上回程的紅眼班機。無從預知的是,飛行由此乖離了原本預想的目的地,變成曲折而輾轉的航線。隔了一日才回到家,打開家門,貓咪們都探頭來看是誰。貓們不擔憂未來。牠們懶得預知更遙遠的未來。牠們只需要知道明天有人在家,日子回到安逸無憂的尋常,會有人陪伴在旁。和千年之人祈望的那麼遙遠的未來,也未必有什麼不同。
#敦煌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