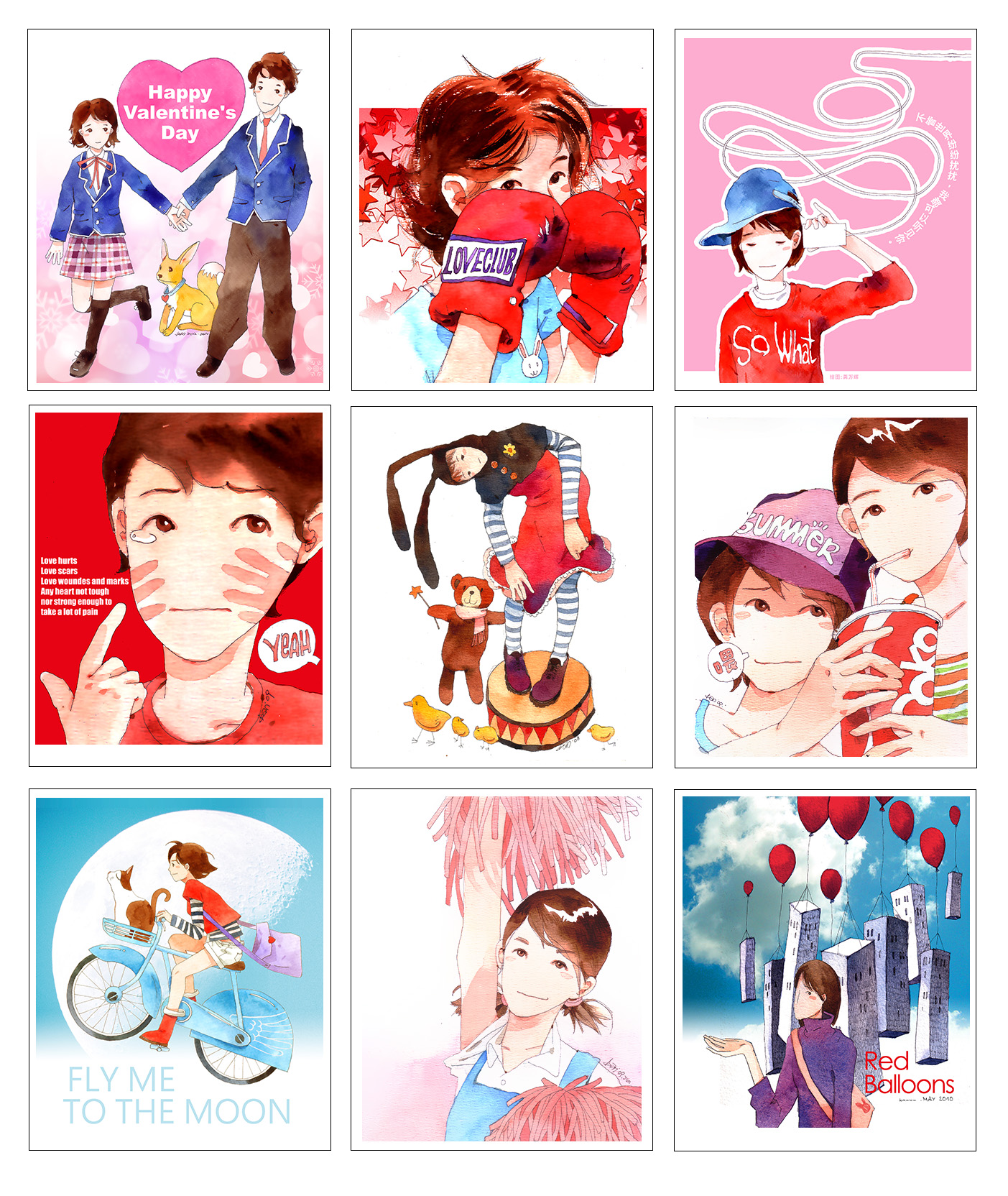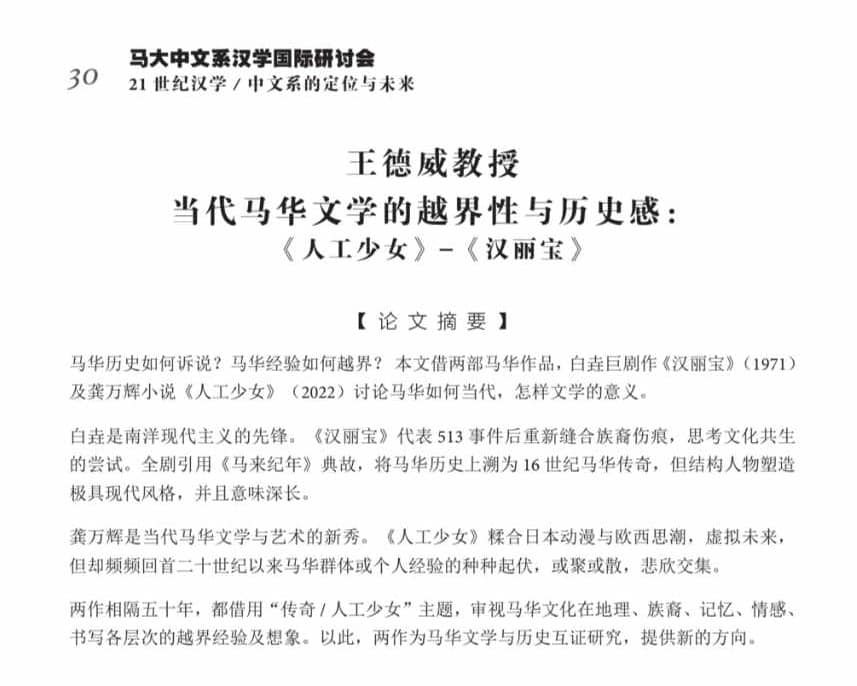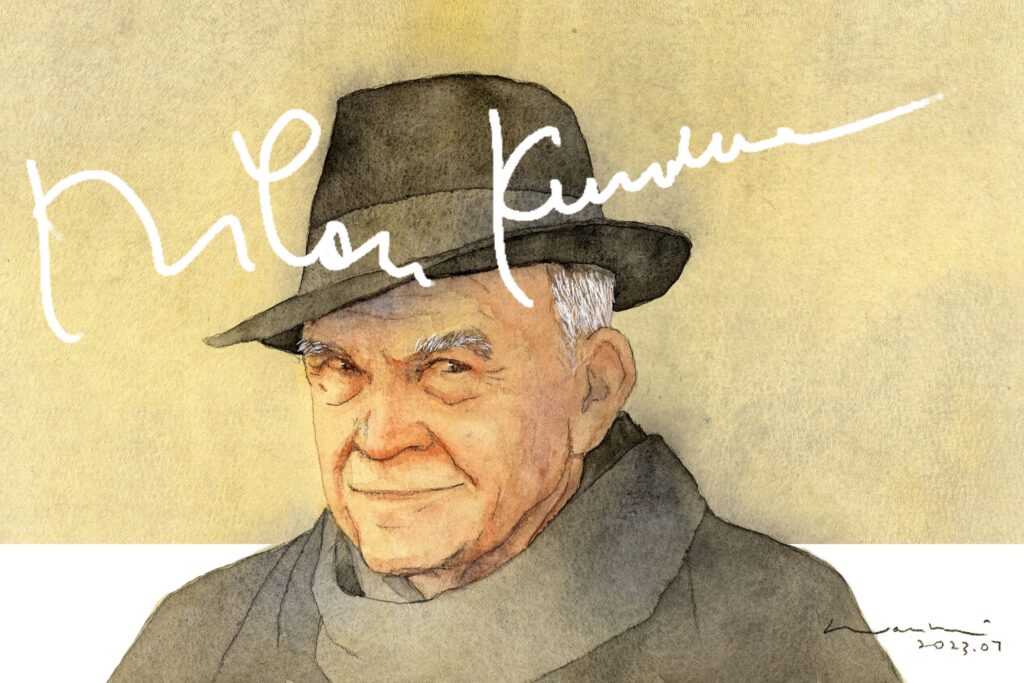2023年過完之後,退租了用來教畫的二樓課室,大概是今年最大的變動。這大半年因為租賃的畫室換了新業主而充滿不確定,虛耗許多心力,終究因為明年租金調漲太高,決定不再續租。近十年的教課時光,教過學生過百,結束實體課也需要一些決心。學生建議換個更好的地點,或者換成工作坊形式,也不是沒想過,或許將來會再籌辦網課,或和其他課室合作,都在考慮中。而接下來也希望留給自己多一些思考和創作的時間。
十一月到檳城參加文學節活動,聽吳明益說起創作者的「創作生命」。創作皆如攀越一座高山,許多創作者已經走過了高峰,也不是不能寫,只是因為年歲、體力,思考方式和應對現實的能力等等各種侷限,必須花費更多的力氣和時間,去面對下坡的道路。吳明益說他自己其實已經在往下的斜坡了。我聽到他如此說,心有戚戚,回想自己虛度多少時光——
能不能再努力拼一下,也許就是拼搏最後一次了,在走過另一個斜坡之前。
今年在誠品、季風帶書店和城邦書店,參與了三場展覽,完成了十五本書的封面設計;在台馬兩地的副刊共刊登了二十五幅插畫,外加為牛油小生新書畫的插圖八幅。《人工少女》出版了一年,仍持續在今年講了九場講座和對談。
年終結算這些時間換來的數字,仍覺得不甚踏實。好像該交的功課沒做完,想頭低低混過去明年的那種心虛感。
下半年,參加了三場葬禮,不知如何話別。
倒是年末約見了熱鬧相聚的年少友人,嘻嘻哈哈,重拾回一些生活的動力。他們皆在上坡的路途上,閃閃發光,讓人羨慕。只有他們才會提出聖誕節交換禮物這樣的提議。我許久未想過為別人買禮物這回事。彼此在笑鬧之間交換禮物,我收到了一支粉藍色的墨水鋼筆。正好。好似每次在活動上為讀者簽書的時候,我總是臨場借筆,現在我有自己的筆了。
物物交換,桃之於李,都是贈禮。
在喬治市文學節見到了久違的香港友人樂敏和黃怡,也認識了新朋友黃言丹和葉梓誦,交換了彼此的書,用心地留下各自的字跡。黃怡問我,新的一年有什麼心願。她像是許願女神那樣,為我寫下了:「願你在這紛擾的世界裡,總有寫好下一部小說的時間和心情。」
離開檳城之前,在旅館Lobby退房之時,巧遇詩人飲江走過,連忙叫住他,又匆匆忙忙打開原本整理好的旅行箱,抽出了他的詩集,讓他簽名。飲江叔叔(我都跟著他們亂叫他「飲江叔叔」)已經七十多歲了,仍源源不斷寫出別出心裁的詩。我好希望像詩人那樣,無謂上坡和下坡,都堅毅前行。所有留下的句子,都是詩人給予這個世界的,時間的禮物。
告別2023年,接下來的日子,期待邀約:
◉ 畫展/聯展
◉ 插畫和特約訂畫
◉ 客座教課/畫室合作
◉ 書籍封面設計
◉ 雜誌約稿
◉ 國內外文學活動,作家駐校、駐村、駐市,各文學節/作家節等
皆可聯絡本人:龔萬輝 wannnhui@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