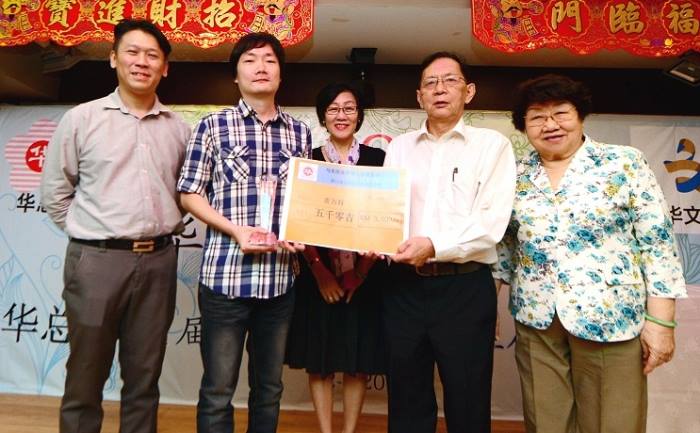──就當作是畢業感言吧
我二十五歲第一次參加花蹤,第一次得首獎。散文組同組的黎紫書得評審獎,當她在下一屆花蹤宣布不再參加徵選獎的時候,我心底想的是:「好可惜,好想再跟黎紫書較一較量啊。」當時的她那麼自信而耀眼,儼然台上唯一的主角,而我是才剛出道的初生之犢。在「後黎紫書」時代,我陸續在同一個競場得了五座銅雕,黎紫書卻已經越走越遠了。
我是一個從文學獎受惠許多的寫作者,依循著花蹤得獎、台灣得獎,爾後出版第一本書的老派方程式而成為一個所謂作家。我近十年來已經不曾參加台灣的任何文學獎,但參加花蹤對我來說卻有著更深切的意義。我把花蹤視為一個自我的磨練,視自己這兩年來有否進步或懶散。而和我同代的寫作朋友們,每一次都交出那麼耀眼的作品──不同路數的風格,更出人意表的題材──那有時太起伏的評審過程和太戲劇化的揭獎結果,真的讓我捨不得離開這個舞台。
我好幾年前在台上說,參加花蹤就好像參加同學會。我是真的珍惜我的「花蹤同學會」的。創作的過程何其孤單,寫作是永遠的單打獨鬥,即使最親密的人也走不進去那種孤獨。所以寫作之外,我總期待兩年一聚的時光,看看朋友,搖旗吶喊一下,交換一下彼此的寫作計劃,拍一拍遠方友人的寬肩,頒了獎照例要去喝酒喇賽。
都說是同學,也就終有一天大家都要畢業。歷經花蹤十多年,銅雕也拿過幾樽,參賽的患得患失也已和少年時大不同了,作品也不再為比賽而寫。共場競技的同輩好友,該立下名字的也都立下名字了,該出書的也都出書了。我不敢確定我們是否完成了一個時代,但我真的不想最後參加文學獎的意義只剩下獵取豐厚的獎金,那真的一點意思都沒有了。
黎紫書當年在全盛時期宣布不再參加徵選獎,我從來都不覺得那是為了禮讓後輩,相反的,我覺得她看見了更遠、更值得去努力的目標。而我要追上她的腳步的話就要讓自己走得更遠。說真的,我其實每次在入圍和得獎名單上看見不認識的名字都覺得馬華文壇很有希望(許怡怡妳是許涼涼的妹妹嗎?)。而我仍然留戀花蹤,仍然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出現在入圍名單裡。花蹤難度更高的競場就是「馬華文學大獎」,以整本書的重量為競逐。我希望我可以交出這樣的創作成果,或許到那時,我終於又可以和黎紫書再交一交手,或者同台的將是更年輕的天才後輩,又或者是更厲害的最終關三大BOSS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這應該可以讓參加文學獎這件事,變得更熱血、好玩一點。
創作的道路上,真的很期待有好朋友,也期待有好對手。而我何其幸運兩者都擁有了。謝謝大家,深深鞠躬。